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實證醫學中心主任、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副主任
謝明諭
成果導向教育教育(Outcome Base Education)的實踐與挑戰
引言
成果導向教育(Outcome-Based Education, OBE)是一種聚焦於學生學習成果的教育方法,強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達成特定的知識、技能與態度[1],隨著醫學教育的發展,OBE的重要性日益凸顯。傳統的教育模式著重於教育者的角度以及教學課綱的規劃,忽略了學生實際獲得的成果。在日益複雜的醫療環境,以及強調跨專業的醫療照護模式中,醫學教育轉型至OBE尤為必要,這不僅能提高教育品質,更能確保未來的醫療專業人員具備所需的能力和素養[2]。
OBE的理論基礎
OBE的核心理念在於學生學習成果的具體、明確和可衡量性。這種教育模式基於以下幾個主要原則:
- 明確的學習成果:課程設計必須界定明確的學習成果開始,而且這些成果必須是具體、可衡量且能反映學生需要掌握的知識和技能。[3]
- 以學生為中心:教學過程應圍繞學生的需求和學習方式展開,教師的角色是引導和支持學生達成學習成果。[4]
- 持續評估與回饋:學習成果應通過多種評估方式進行評估,並且要有系統的回饋機制,幫助學生不斷改進。[5]
OBE與傳統教育模式的最大區別在於前者更強調學習者的最終學習結果,而非根據課程、課綱為主的授課過程。傳統教育側重於教學活動本身,教師是教學的中心,學生被動接受知識。而在OBE中,學生是學習的主體,教師更多地扮演引導者和協助者的角色。[6]
定義成果的挑戰
在實施OBE的過程中,明確定義學習成果是最重要的一步。然而,這一過程也充滿挑戰。首先,學習成果必須具體且可衡量,但醫學教育中的一些能力和素養(如臨床判斷和人際溝通技巧)往往難以量化。[7] 其次,學習成果的定義需要廣泛的共識,這需要教師、學生和醫療行業的參與者共同努力。此外,學習成果應具有靈活性,以適應不斷變化的醫療環境和學生的個體差異。[8]
設計和實施OBE課程
設計成果導向課程的步驟包括:
- 確定學習成果:根據醫學專業的要求和標準,確定學生需要達成的具體學習成果。[9] 對於不同階段的學習者,應建立該層級所需應對業務的能力作為學習目標,需要在學生、教師以及臨床單位中建立共識,是最重要的一步,也是最不容易的一步。
- 設計課程內容:根據學習成果設計相應的課程內容和教學活動,確保每一環節都能幫助學生達成預期成果。[10] 以實習醫學生外科學習為例,如果要達成基本的消毒、鋪單以及無菌技術,就必須安排在手術室的實作課程。
- 選擇評估方法:設計多樣化的評估方法,包括理論考試、臨床技能測試、案例分析等,以全面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果。[11] 有好的測量才能知道學生能力的落差,調整學習策略,也才能做好最佳的教學管理。
- 實施教學活動:教師應根據課程設計進行教學活動,並在過程中不斷調整教學方法,以適應學生的學習需求。[12] 這可以是大堂課程、小組討論,或甚至線上課程,讓學生在臨床單位學習時,可以隨時取得資源來解決臨床照護問題,逐漸將知識內化成經驗與能力。
- 提供回饋與支持:通過持續的評估和回饋,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的學習進展,並提供必要的支持和資源。[13]
評估與回饋
這是OBE相當重要的部分,就像在做練習題時,我們會先把答案遮起來,先答題之後再對答案一樣。在學生先完成一定的照護目標,經過老師評估其優缺點後,回饋給學生的知識才能成為經驗與能力的一部分。評估學習成果的方法應多樣化,以全面反映學生的知識、技能和態度。[14] 除了傳統的筆試和實踐操作考試外,可以加入案例討論、模擬病人演練等方式。這些評估方法不僅能檢測學生的學術能力,還能評估他們在實際臨床情境中的表現。[15] 基於成果的回饋機制則是OBE的重要組成部分。教師及時向學生提供回饋,幫助他們辨識自己不足之處,並指導他們改進學習方法。[16]
案例研究與實踐經驗
全球許多醫學教育機構已成功轉型至OBE模式。例如,根據Frenk等人(2010)的研究,全球多所醫學院在醫學教育改革中強調成果導向教育(OBE),學生的臨床技能和理論知識水平顯著提高。[18] 這些學校的做法是:首先,詳細定義各個課程的學習成果,並將其與醫學執業標準對接;其次,採用多樣化的教學方法,如PBL(問題導向學習)和CBL(案例導向學習),幫助學生在真實情境中應用所學知識;最後,設計了綜合性評估系統,定期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果,並根據評估結果進行課程調整。
中山醫學大學於2001年開始引入問題導向學習(Problem-Based Learning, PBL)教學模式,並於2002年開始推行模組教學,迄今已經超過20年。模組教學促進學生對學科知識的整合應用,通過系統化和結構化的課程設計,使學生能夠在學習過程中不斷鞏固和應用所學知識。這些教學改革措施有助於提升醫學教育的品質,確保學生在理論知識與臨床技能上均衡發展,為未來醫療職業生涯做好充分準備。同時,在PBL的教學模式中,透過小組合作和討論來解決問題,提升了學生批判性思考、自主學習能力及團隊合作精神。從參與課程的學生自行分派工作、自己安排學習計畫,並在互相分享學習成果時,他們收穫豐盛。每位擔任tutor的老師都可以感受到學生滿滿的學習熱忱,並觀察到學生在自主學習和問題解決能力上的顯著提升。這種教學方法不僅能更好地幫助學生應對臨床實踐中的挑戰,還能促進理論與實務的結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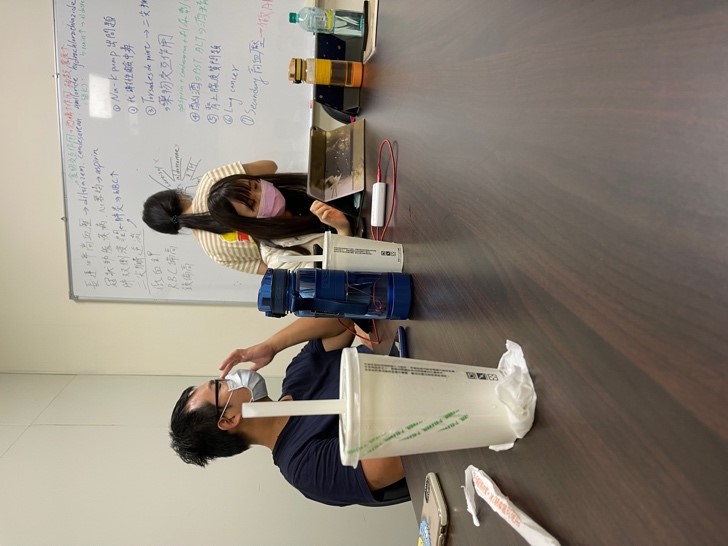

挑戰與未來的展望
OBE的實踐過程中也面臨許多挑戰。例如:教師以及教育單位需要轉變教學觀念,從傳統的知識傳授者轉變為學習的引導者和支持者[20];此外,評估工具的設計和應用也需要不斷改進,以保證其科學性和有效性。[16]
隨著醫學教育的不斷發展,OBE將在未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。技術進步為OBE提供了新的機遇,如利用大數據分析和人工智慧技術,可以更準確地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果,並提供個性化的學習模式。[17] 同時,醫學教育的國際化趨勢也促使OBE成為一種全球化的教育模式,有助於提高醫學教育的標準化和品質。[18]
結論
總結來說,OBE在醫學教育中的應用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。通過明確定義學習成果,設計以學生為中心的課程,並採用多樣化的評估和回饋機制,可以顯著提高醫學教育的品質。[19] 儘管在實施過程中面臨諸多挑戰,但只要各方共同努力,OBE必將成為醫學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。對於醫學教育者來說,不斷學習和實踐OBE理念,將有助於培養更多具備綜合能力的優秀醫療專業人員,從而推動醫療行業的持續發展和進步。[20]
- Harden, R. M. (2007). Outcome-Based Education: The Future is Today. Medical Teacher, 29(7), 625-629.
- Spady, W. G. (1994). Outcome-Based Education: Critical Issues and Answers.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Administrators.
- Harden, R. M., & Crosby, J. R. (2000). AMEE Guide No 20: The Good Teacher is More than a Lecturer - The Twelve Roles of the Teacher. Medical Teacher, 22(4), 334-347.
- Gibbs, G., & Simpson, C. (2004). Conditions Under Which Assessment Supports Students’ Learning. Learning and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, 1(1), 3-31.
- Prideaux, D. (2003). ABC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in Medicine: Curriculum Design. BMJ, 326(7383), 268-270.
- Schuwirth, L. W., & Van der Vleuten, C. P. (2011). General Overview of the Theories Used in Assessment: AMEE Guide No. 57. Medical Teacher, 33(10), 783-797.
- Shumway, J. M., & Harden, R. M. (2003). AMEE Guide No. 25: The Assessment of Learning Outcomes for the Competent and Reflective Physician. Medical Teacher, 25(6), 569-584.
- Epstein, R. M., & Hundert, E. M. (2002). Defining and Assessing Professional Competence. JAMA, 287(2), 226-235.
- Boud, D., & Molloy, E. (2013). Rethinking Models of Feedback for Learning: The Challenge of Design. Assessment & 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, 38(6), 698-712.
- Norcini, J. J., & McKinley, D. W. (2007). Assessment Methods in Medical Education.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, 23(3), 239-250.
- Hattie, J., & Timperley, H. (2007). The Power of Feedback.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, 77(1), 81-112.
- van Mook, W. N., de Grave, W. S., Wass, V., O'Sullivan, H., Zwaveling, J. H., Schuwirth, L. W., & van der Vleuten, C. P. (2009). Professionalism: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.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l Medicine, 20(4), e81-e84.
- Barrows, H. S. (1986). A Taxonomy of Problem-Based Learning Methods. Medical Education, 20(6), 481-486.
- Thistlethwaite, J. E., Davies, D., Ekeocha, S., Kidd, J. M., MacDougall, C., Matthews, P., ... & Clay, D. (2012). The Effectiveness of Case-Based Learning in Health Professional Education. A BEME Systematic Review: BEME Guide No. 23. Medical Teacher, 34(6), e421-e444.
- Harden, R. M. (2002). Developments in Outcome-Based Education. Medical Teacher, 24(2), 117-120.
- Norcini, J. J. (2003). Peer Assessment of Competence. Medical Education, 37(6), 539-543.
- McGaghie, W. C., Issenberg, S. B., Petrusa, E. R., & Scalese, R. J. (2010). A Critical Review of Simulation-Based Medical Education Research: 2003-2009. Medical Education, 44(1), 50-63.
- Frenk, J., Chen, L., Bhutta, Z. A., Cohen, J., Crisp, N., Evans, T., ... & Zurayk, H. (2010). Health Professionals for a New Century: Transforming Education to Strengthen Health Systems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. The Lancet, 376(9756), 1923-1958.
- McLean, M., Cilliers, F., & van Wyk, J. M. (2008). Faculty Development: Yesterday, Today and Tomorrow. Medical Teacher, 30(6), 555-584.
- Prideaux, D. (2007). ABC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in Medicine: Educational Strategy and Curriculum Design. BMJ, 326(7383), 268-270.
